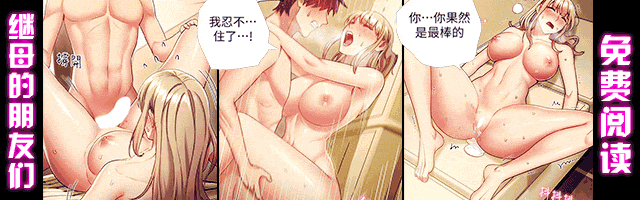行方长放弃了。
他的力量,他的思绪,他的确一切一切,都停了下来。
——反正现在他的生活,也就与“死”无异,那么,为什么不干脆放弃呢?
内心一隅的软弱正在呼唤着他,他最终叹息一声,同意了那卑微、怯懦的想法,就像他先前曾做的那样,放任自己沉没。
他被击沉了——全身上下都覆盖着精液、巨大的肛塞确保他小腹里的东西不会溢出去、双手被拷在身后、身上的鞭痕散发着甜美的疼痛——他以这种淫乱又不堪的姿态被击沉了,彻彻底底。
过了很长时间,那个施加这些所有的人走了进来,他发现行方长已经醒了,却没有睁开眼睛。
“呵……”他发出一声低笑,“我说过,你喜欢这样……”
那个眼罩又一次回到了行方长的眼睛上。
他的主人将他从地上拉起,因为姿势的改变,肛塞更深入了,行方长发出一声闷哼,只觉得自己小腹里有什么东西在响。
“现在……”身前传来了那人满是欣喜的声音,“你是我的了。”
行方长呜咽一下,颤抖着回答道:
“是的,主人……”
…………
……
于是,“行方长”消失了。
他辞了工作,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在人们面前。
而在小方家里,则多了一个鸟笼。
那笼子上缀满花纹,用各式各样的小装饰精心妆点得美好无比;可这仍然改变不了它是个笼子的事实,它唯一的出入口时常都上着锁。
它就是行方长新的住处,他的主人铺了足够的软垫来让那里面变得十分舒适,但它不够高,大部分时间里,他只能跪坐在里头。
事实上他也不被允许独自站立,必要的时候,他的主人会牵着他的狗链,让他爬行到要去的地方。
一开始,他并不习惯这样,然而一件事一旦做久了,不习惯也得变成习惯。
现在他几乎已经忘了直立行走的感觉,他每天早晚都被主人牵出笼子,这两个时间是他吃饭的时间。
而晚餐后,主人会拍拍他的屁股,行方长会会意,他抬起下身,淫荡地摇晃着臀部:
“求主人……享用我的身体……”光是这些台词就让他的身体燥热,“请、请您……操我……”
然后他会得到他请求的。
无论如何,最后他都会得到他请求的,无论是温柔的还是粗暴的,无论是疼痛的还是精疲力竭的。
他的主人会让他趴在地上、像狗一样操弄着他,那项圈仿佛使这个幻想变成了实质上的现实,他的主人甚至会拍着他的屁股,问他:“小狗,喜欢吗?”
那时行方长就只能呜咽着发出两声狗叫,作为他最好的回应。
现在,他的主人也拍着他的臀瓣,低声笑道:“选一个。”
他前摆着许多个安全套,他能听见主人把它们放在地上,一字排开,像这是什么抓周仪式。
而他看不见它们——他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光了,他的眼罩很少会被摘下,只有当它需要换新时,他的主人才会如此大方。
行方长时常会觉得,他再也见不到光了,不可思议的,他并未感到任何遗憾。
他手脚并用地在地面爬行了一小段,在数个塑胶味道间迟疑了一会儿,最终叼起其中一个。
身后又一次传来了低笑,那人说道:“选得好。”
行方长呜咽一声。
他先前已经被狠狠操过了一次,那些白浊此时此刻正在他翘起的屁股里。
因为姿势的缘故,它们顺着甬道一路向下滑去——他的主人让他不要把他的东西漏出身体,否则就要受到惩罚。
想起惩罚时的疼痛,行方长的呼吸不由得变得有些粗重,在他还能朦朦胧胧的想起来的那天里,他的双腿上后来满是鲜血。
那鲜血是鼠蹊部被三角木马磨破的皮与被散鞭打出的,他的主人用双氧水为他消毒,他疼得忍不住蜷起身体低声哭泣。
主人说:“这是代价。”
是的,代价。
行方长泪眼模糊地接受了这个解释。
因为主人的话就是绝对,毕竟他在模模糊糊与支离破碎间唯一能抓住的就是那个声音,用布蒙住后刻意伪装出的声音。
——若是以往的行方长一定能注意到,即便在他已经知道对方身份后,他以本音说话的次数仍不多。
伪装对昔日的陌生人来说绝不仅仅是需要那么简单。
而现在的行方长不会去想这些……他根本不在乎这些,他是具空壳、他副行尸走肉。
但这纯粹皮囊却能够感受到快感,例如现在正在他柔软后穴里抠挖的手指——那仅仅是一根手指,插入了方才被更大东西进入过的地方。
“哈啊……!”饥渴的肠壁紧紧缠上了手指,“嗯……!”
那根手指毫不费力地戳刺到了他的敏感点,
它在早已被精液湿润的后穴里毫不费力地挖掘着。
“嗯、嗯嗯——”行方长长长地呻吟着,身体摆动起来迎合着手指的挖掘,他知道这么做他的主人会心情愉快。
主人的愉快也会令他快乐——或者至少让他不受苦——这点已深深地印刻在了他身体深处。
一根手指变成了两根。
与此同时,自他身后又传来了那低笑声:
“淫乱的小东西。”他说,“你是吃什么长大的?”
“我……呜……”说些什么能让主人高兴?这个问题他根本不用想,“是吃、主人的……精液……”
是的,他是被用精液饲养的。
行方长迷迷糊糊地想,那两根手指正揉捏着他敏感点,有那么一会儿他以为它们会夹住他的肠壁。
他觉得自己全身上下的敏感点都被对方捏在手中,随着他的一举一动上下欺负颠簸,他一动、行方长便发出让他满足的呻吟。
“呜、呜呜……哈啊……”
有时侯他会觉得自己像是个弹奏快感音韵的乐器。
有时候他又会觉得自己是个专为承载快感而生的容器。
更多的时候他会觉得,他天生就是为了被男人进入、操弄,成为他欲望的发泄品。
可在他的幻想中没有一个他是人,不,他已经彻底失去了那个身份,他在区区两根手指下翻覆呻吟,他的欲望仅仅在这样的刺激下就涨得发疼。
“射出来。”主人命令道。
“我、呜……不……嗯嗯……”
他下意识地拒绝了,幸好声音被淹没在了呻吟声中。
而更幸运的是他的身体远比他要诚实,在主人这样说的下一秒,就颤颤巍巍地发泄而出。
“哈啊、哈啊啊啊!”
第三根手指撑开了内里,行方长眼罩下的双眼已彻底朦胧。
可直到这时他才听见了安全套被撕开的声音,他知道接下来还会有更多事在等待着他,他喘息着,争取让更多空气进入肺部。
——他不是没有被整夜折腾的经验。
那个夜晚简直不忍回想,他被吊着,身体与地面只有一边足尖接触着地面。
而他的下身则被贯穿着……被按摩棒或者男人的欲望,他被不断贯穿着,一整夜都没有停下。
到早上他已经无法射出任何东西,一落地便下意识地向主人靠了过去,他在精疲力竭中被温柔地抱住了,并在那拥抱中彻底昏了过去。
现在,想到那时绵长又无尽的快感,他几乎要痛哭出声,然而快感同样是那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他们一起向他袭来——如同那之外的众多记忆一般。
行方长颤抖着感受那三根手指的扩张,他知道主人已经把安全套套上自己的欲望,但他对那东西何时才会进入自己一无所知。
他好奇自己到底挑选了些什么。
然后这一闪而逝的好奇彻底泯灭在了快感中。
……对了,除了这些,他什么也不需要。
手指好像又挺进了一点,它们并排在他体内,行方长啜泣着抠住地面,却又很快被拽回来搭在自己的臀上。
无须更多指使,行方长无师自通地掰开了自己的臀瓣,穴口被拉扯得变了形,他发出一声短促的抽泣,觉得自己的内里已经被手指操出了水。
“就算是最贱的贱货也没有这么多水。”似乎有声音在他耳边回荡,“就算我塞进一个拳头进去,你也会开心地接受吧,嗯?”
“呜啊!呜……呜呜……”他会,并且他们已经尝试过了。
那是个类似现在的清醒,他的主人在他的后穴里不断加入着手指,一根又一根……
可直到他试图把最后的大拇指塞进那个入口,行方长才意识到他想做些什么。
主人的手在他身体里握成拳,不断地深入内里,鼓捣出一堆又一堆行方长不知道是什么的黏糊声。
他尖叫、他惨呼,他的所有声音都似乎在那个晚上穷尽,但到了最后——没错,他呻吟着,在拳头下射了一次又一次。
行方长觉得自己正在变得越来越可怕。
那种恐惧感深深地源于他的内心,呼啸着将他吞没成了某种不可名状之物。
“啊、啊!”现在他在三根手指下颤栗,“主人、呜……求您……”
“求我做什么?”
“呜啊、求您……求您……”他的声音已经在手指的操弄下变得绵软无力,正是主人喜欢的那种,“……操我……”
“真是饥渴的屁股。”手指抽了出来,它们带出些许粘液,被它们的主人抹在行方长嘴边,“很想知道你挑选了个什么,嗯?”
行方长的嘴唇颤抖着,缓缓吐出那个字:“想……”
是的,他想知道……他渴求知道……是什么将要进入他的身体——主人准备的安全套从来都不会是什么善良之物。
他听见身后人起身,当他走至身前时行方长抬了抬头
,他的动作牵引着胸口乳环动了动,发出一串清脆的声响。